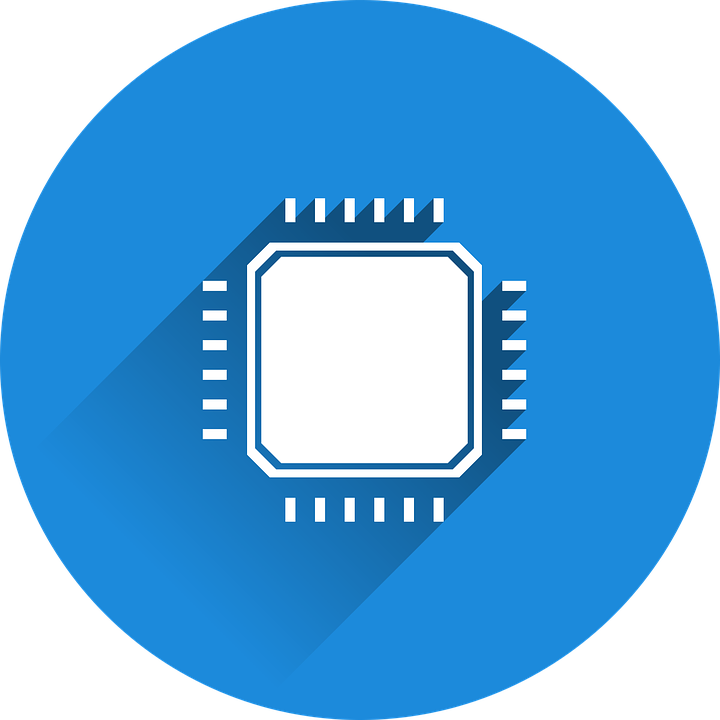安史之乱爆发原因综述
摘 要:始于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历来被认为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节点,一生因此颠沛流离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在其诸多著名诗歌中对此进行了生动描述。浩劫过后盛唐不复存在,昔日的大唐成为后世王朝的终极目标,甚至也是当下的复兴目标。然而,对于造成这场叛乱的原因,多数人都将其归结为李隆基的昏庸与李林甫、杨国忠等大臣的专权误国。这种解释似乎表明若有一位贤明的君主当政,则类似危机就不会爆发了。很显然,这种解释放大了“人”的影响力,并未对危机背后各种客观因素的相互作用进行全面分析,因而没有正确阐述安史之乱爆发的根本原因。本文试图从唐朝的“均田制”、“府兵制”、“节度使”、“羁縻政策”等经济政治角度出发,阐明安史之乱是一系列“算法”运作下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均田制;府兵制;节度使;羁縻政策
一. 均田制的瓦解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既然要探究安史之乱爆发的根本原因,就不得不对当时的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公元485年(北魏太和九年),冯太后依照大臣李安世的建议颁布“均田令”,“均田制”系统就此开始。“均田制”的创立在当时安顿了大量流离失所的农民,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并且保证了中央财政的来源。隋朝继承并发展了该制度,唐承隋制,“均田制”也因此成为唐朝前期的经济基础。据史书记载,隋朝末年“六军不息,百役繁兴,行者不归,居者失业。人饥相食,邑落为墟”[1],虽然其中不乏夸张的部分,但不难看出隋末社会经济萧条,土地荒芜严重,人口锐减,户数2000000余[2]。这正与“均田制”出台时期社会状况有诸多相似,也恰好为唐初实施“均田制”奠定了基础。
唐初的“均田制”是成功的,农民得到土地,农业生产恢复,人口急剧上升,天宝元年的户数为8525763[3],人口为48909800[4],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和经济都是十分发达的。可就在这盛世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机。从公元613到公元713,整整一百年,不用交税的贵族官僚积累了大量财富,通过合法或者非法手段将许多公田据为己有,随着人口的增多,人均土地占有量下降,再加之小农的生存能力本身并不高,破产时有发生,因此土地兼并是必然的。在开元年间出现了“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5]。国有土地的减少,农民受田不足,为了躲避课税,逃户越来越多,“时天下户版刓隐,人多去本籍,浮食闾里, 诡脱繇赋,豪弱相并,州县莫能制”[6]正是当时的真实写照。据记载,天宝十三年“户九百六十一万九千二百五十四,三百八十八万六千五百四不课,五百三十万一千四十四课”[7],也就是说登记在户的只有不到百分之六十需要交税,本身交税的人数就不多,再加之大量逃户且政府开支并未收缩,朝廷财政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开元十年,唐玄宗在一次诏令中提到“租赋颇减,户口颇虚”[8],可见此时的“均田制”已经名存实亡,国家的经济基础也越发不牢固。
二. 府兵制的结束
府兵制是均田制的一个产物,由西魏丞相宇文泰开创,本质是为中央政府提供稳定可靠的兵源。这套制度经过隋朝的完善——与均田制彻底结合,在唐朝呈现出寓农于兵的特点,即武装集团里寄托生产,正如白居易在《登阊门闲望》中写到:十万夫家供课税,五千子弟守封疆。按照唐朝的规定,只有户口为上等或中等的民户,且自己愿意当兵的,才由政府挑选出来。当兵人家的租庸调是豁免的,但是物资都是自备,“凡火具乌布幕、铁马盂、布槽、锸……钳、锯皆一,甲床二,镰二……矢三十,胡禄、横刀、砺石……行藤皆一,麦饭九斗,米二斗,皆自备,并其介胄、戎具藏于库。”[9]这套系统初衷是中央为了保证有大量兵力的同时,尽可能地减少军费开支,因此唐太宗并不像汉朝初建时休养生息,而是依靠大量的府兵却耗费少量国库的钱财征战四方。但随着均田制的瓦解,农民授田愈发不足,因此无法负担府兵的费用。钱穆在其名作《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还做出以下阐述“第一,各地府兵都要到政府轮值宿卫……后来天下太平,每常几万人轮番到中央,没有事情做……士兵变成了苦工,受人鄙视……第二,在唐初,府兵出外打仗阵亡,军队立刻把名册呈报中央,中央政府也马上会下令给地方,立刻由地方政府排热到死难士兵家里去慰问,送他勋爵,给他赏赐……到后来,军队和政府,还是犯了一个松懈病……本来府兵打完仗就要复员,现在变成没有复员了,让你长期戍边。”[10],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充当府兵,最终“折冲诸府无兵可交”。
三. 节度使权力扩大
唐太宗在位时期,国家依靠强大的府兵开疆拓土。唐太宗去世后,边境之外各方少数民族又开始“反扑”,并且灭国所带来的红利大不如从前,所以这时候国家的军事战略改为防御。可是随着府兵制的破坏,国家的军事力量下降,如果守不住现有的土地,这对本身土地就“不够”的“均田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怎么解决边境的防御问题就成了唐帝国的头等大事。
节度使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的,其设立本意是方便朝廷解决边疆问题。到了唐玄宗的时期,朝廷改府兵制为募兵制,但是因为均田制——经济基础已经彻底败坏,中央无法提供足够的物资供养大量戍边战士,于是节度使获得了地方征兵权和财政权,以求达到自给自足,“以方隅底定,令中书门下诸道节度使,量军镇间割利害,审计兵防额定,于诸色征人及客户中召募丁壮,长充边军,曾给田宅,务加优恤”[11]。节度使因为具有募兵和财政权,可以训练出作战能力强的部队,比如王忠嗣、哥舒翰等节度使令唐军实力增强,不但灭了突厥,还击败屡次来犯的吐蕃。《资治通鉴》记载“自唐兴以来,边帅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名显著者往往入为宰相”[12],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事愈发频繁,故无法频繁调动节度使来防止其发展个人武装力量,这就打破了原先“不久任“的传统,并且为了让节度使更好地应对战争,鉴于初期节度使的良好表现,朝廷将权力不断下放给节度使,因此很多节度使身兼转运使、镇守使、采访使等职务。节度使有着各项权力,又能长期在一方任职,而且有些边疆节度使逐渐擢用武人(安禄山正是武将出身),这些因素的作用下自然而然会有节度使拥兵自重,正如史书所言“及府兵法坏而方镇盛,武夫悍将,虽无事时,据险要,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然则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13],钱穆指出“现在专说唐代,似乎其中央行政比汉代进步,而地方行政则不如汉……而由军队首领来充地方行政首长,则是更大毛病。唐室之崩溃,也可说即崩溃在此一制度上。”[14]
四. 羁縻政策的局限
上文提到设立节度使是为解决边患问题,这就不得不提唐帝国与四周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唐朝对于四方少数民族的管理政策概括起来——羁縻制。羁縻政策包含贡赐、互市、册封、设立羁縻府州、和亲。唐人对于少数民族是相对包容的,因此羁縻府州的设立给予了少数民族上层较为充分的自治权,并提高了少数民族经济、文化、教育水平,这就为安史之乱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史书明确记载“燕州以下十七州,皆东北藩降胡散处幽州、营州界内,以州名为羁縻之”[1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羁縻府州内安置了大量投降的胡人。身为少数民族,骑射是他们的长项,因此军事训练成本远远低于同等规模的汉人。唐朝政府正是看到了他们具有这样的先天优势,便征调他们开疆拓土。特别要指出的是,这些外族士兵和将领是在唐朝进行短期急剧扩张时收编的,唐朝对于他们的思想改造程度令人怀疑,即便是成功同化,一旦中央军事力量下降,中央集权与羁縻府州分权也会产生矛盾。
贞观过后不久就产生了暴动,公元682年阿史那骨笃禄趁武则天擅政,以熟知唐边境的阿史德元珍(原为单于府检校降户部落官员)发动叛乱建立可汗国,诣在恢复昔日突厥的霸业。直到公元745年,唐朝与回鹘才攻灭后突厥汗国。陈寅恪认为这段时间河朔地区发生胡化,改变了河朔地区原来的结构,“可知东突厥复兴后之帝国其势力实远及中亚,此时必有中亚胡族向东北迁徙者。史言‘默啜既老,部落渐多逃散’, 然则中国河朔之地不独当东突厥复兴盛强之时遭其侵轶蹂躏,即在其残败衰微之后亦仍吸收其逃亡散离之诸胡部落,故民族受其影响,风俗为之转变, 遂与往日之河朔迥然不同, 而成为一混杂之胡化区域矣”。[16]
府兵制的结束,募兵制开始,节度使也就掌握了征兵权和财政权,正如上文所讲征用胡人为兵是节省开支的做法,再到后来节度使可以擢用武人,“夫此区域之民族既已脱离汉化,而又包括东北及西北之诸胡种, 唐代中央政府若欲羁縻统治而求一武力与权术兼具之人才,为此复杂胡族方隅之主将,则柘羯与突厥合种之安禄山者,实为适应当时环境之唯一上选也”[17] 。节度使雇佣胡人为兵本身就存在风险,而以胡人为一方节度使,且在中央军事力量下降的情况下,更是加大风险。
另一方面,玄宗时期为了应付吐蕃、突厥,兵力主要集中在西北,故幽州地区状况发生了变化,“先天元年十一月,乙酉,奚、契丹二万骑寇渔阳,幽州都督宋景闭城不出,虏大掠而去,开元二年,初,营州都督治柳城以镇抚奚、契丹,则天之世,都督赵文翙失政,奚、契丹攻陷之,是后寄治幽州渔阳城”[18]唐朝政府为避免两线作战,不得不对幽州地区的奚和契丹示缓,主要采取羁縻制度中的和亲方案,从开元五年到天宝四年,永乐公主、燕郡公主、东华公主、静乐公主都是下嫁契丹。玄宗曾对契丹使者说“卿之蕃法多无义于军长,自昔如此,朕亦知之”[19],可见唐玄宗实际上是知道危险的,但是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不得不对其采取羁縻制度,所以安禄山最终能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可看作这种羁縻制度的产物。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唐初以均田制为经济基础,并配套施行府兵制,迅速开疆拓土,羁縻大量外族,实力在短时间内达到巅峰。然而这样的繁荣、自信却干扰了人们对时局的判断,并未及时主动对政策革新,而是在“均田制”“府兵制”“羁縻政策”上越陷越深,所以安史之乱正是这一系列“算法”运作下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1]《隋书》帝纪第四,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
[2]《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3]《旧唐书》本纪第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4]《旧唐书》本纪第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5]《陆宣公集》卷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6]《新唐书》宇文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7]《旧唐书》本纪第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8]《唐大诏令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
[9]《新唐书》志四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10]《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11]《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 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12]《资治通鉴》 唐纪.,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13]《新唐书》兵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14]《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15]《新唐书》卷三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16]《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17]《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18]《资治通鉴》 卷二百一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19]《资治通鉴》 卷二百一十四.,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